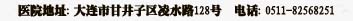忆父亲
湛波(贵州)
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我很悲痛。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用最短的时间赶到父亲身边,看父亲最后一眼。
但我还是迟到了。回到老家,看到的是父亲冰冷的身体和那早也僵化的面容。我知道,父亲已经艰难地走完他78年人生历程,与世长辞。他静静地躺在老家堂屋里,嘴巴还张着。我知道他想说:老五,你回来啦!可是,那熟悉的声音从今以后不会再响起,早已和他那僵化的面容一起地留入了我恒久的记忆。
我此时能做的,也只有跪拜,三叩首,任凭泪水模糊父亲的面容。然后,从记忆深处搜索关于父亲的点滴。
父亲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是中国灾难最为深重的时代,仿佛就注定了父亲的一生将与艰难与苦难相随。祖父是单传,居绥阳伞水中街,由于地主相欺,佃户出身的祖父只能迁居新舟桂花大堰子,后再迁居马家屋基――即现在的老屋。由于祖父懒散,家庭的重担就过早地落到了父亲的身上,让父亲一辈子从未进过学堂。叔父8岁那年,祖母撒手人寰,从此祖父更一蹶不振,成天与酒和鸦片相伴。大叔父整整12岁的父亲从此完全地担起了家庭的重担,赡养祖父,供叔父上学,并一直到初中毕业。三年自然灾难时期,勤劳的父亲有幸从生产队长调到公社菜油房,不但能保住自己的口粮,还能利用工作便利救助其他人,善良的父亲为救祖父和叔父的命,眼睁睁地看着我素未蒙面的5个哥妹先后饿死。长年的劳累,更让父亲过早地染病。生我那年,父亲终于病倒,并且病得很重,医院医生都不再接收。正在月子里的母亲因为家庭的贫困只能让父亲呆在家里等待时日,同时用一些民间偏方让父亲治病。不知是上天赐福,还是民间中草药发挥了作用,父亲奇迹般地好了起来。父亲也觉得非常幸运,经常对我说:你多大,我就多活好多年!
从我记事时起,我眼中的父亲就是凶暴、慈祥、严厉的综合体。我小时记得父亲经常和母亲吵架,有一次在吃饭时吵得很凶,父亲将吃饭的碗砸在母亲的头上,鲜血直流,我们几姊妹害怕得连饭都不敢吃,躲在一角静静的不敢说话。同样,我们几姊妹犯错,不用说,先是一顿打,然后叫到咸菜坛子面前跪,跪到他心软了,才叫起来。他不叫起来,是不能起来的,不然又是一顿打,并且比第一次打得更重。记得有次三哥欺负我,父亲抓起扁担就打,还要跪瓦砾,三哥害怕了,晚上跑了出去,躲在房边的稻草堆里,用干稻草将自己埋起来,硬是让父亲和全生产队的人找了一晚上都没找到。有一个大年三十晚上,我记不起也犯了什么事,被父亲打后,还叫我滚,倔强的我真的就“滚”了,跑到我家后面的坟堂里睡着了,父亲找到后把我抱了回去,并且保证说以后不再叫我滚了。
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这句话在我们父子之间体现得淋漓尽致。小时候,我家里很穷,一年有大半年要吃包谷饭、麦子饭,但我从来不吃,宁愿饿也不吃。父亲没法,只得让母亲单独煮一点白米饭留给我,如果几个哥要争,就是一顿打。由于家里穷,大姐小学毕业就辍学了,三个哥相继读完初中,也被迫停了下来,就留我一个人读书。有很多次,父亲为跟我借学费转了好多亲戚和朋友家,而从不同意我停学的要求,现在回忆起他那因未借到钱而失落和劳累的样子,我很悲痛。我考上学校那年,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了,东挪西借基本凑足我的学费后,我在学校的生活费再也无着落了,父亲痛下决心,将自己辛苦多年、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棺林材卖了,并将卖棺林材的元钱亲自给我送到学校,而年少无知的我,竟没有让父亲进校门,拿了钱后就追他回家。这,将成为我一生的遗憾。
我参加工作后,父亲已经渐渐老去了,不再有原来暴躁的脾气。我每次回家,他总是安静地坐在那里,轻意细语地跟我讲做人的道理。父亲虽然没有进过学堂,但他艰难一生的阅历为他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变成他那平实的话语,跟我娓娓道来,让我受益非浅。他常说:人一旦有害人之心,就会害已。父亲一生,从未害人,而更多的是救人。因而他从无遗憾,走得那么安然。
随着我工作的变动,工作的地点离家越来越远,工作的时间也越来越紧张了,而回家看望父亲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起来。不知不觉中,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年,父亲再一次病重。在我的竭力主张下,父亲医院治疗。高血压、冠心病、肺气肿、哮喘病等多种病症齐集父亲一身。出院后,父亲已经不能断药。年,医院检查,医生确诊父亲的肺只有三分之一功能正常,其余基本坏死,并且体内多处功能器官基本老化、坏死,也无住院治疗的必要。知道全部病况的父亲,并没有因此而悲观绝望,反而坚强地活着。年,药物对父亲已经基本不起作用,只能靠间歇的输液排出体内腹水,补充体能。走路也越来越困难,但他坚持每天吃饭,用他的话说:只要吃得,就没得事。
最后一次与父亲相处,是去年除夕。吃完年夜饭我就和父亲坐在火边,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父亲是看不懂的,他只喜欢看唱戏的段子。我知道父亲是想多陪我坐坐,所以我一边看,一边跟他说话。我说了我的工作近况,他非常满意,反复说我是他的骄傲。谈到他的病情,我要他多走动,坚持吃饭,应该还要活几年,他频频点头。春节联欢晚会结束了,母亲催了他好几次,要他去睡,他不去,说我工作忙了,不容易回来,要多陪陪我。现在想来,是不是因为他已清楚那是和我的最后一次相处,才久久不愿去休息。如果我当时知道,我宁愿陪他坐到天亮。
遗憾的是,一切都不会重新再来了,父亲已经离我而去了。回想起正月初一向他辞行时他那木然而失落的表情,回想起以前每次回去离家时他站在屋边那佝偻静立、久久目送的身影,回想起因病魔缠身他那艰难挪动的脚步、粗粗的喘气声,我的心,只有痛。
几次的坚持,让父亲延缓了好几年的生命,这是我的欣慰;太少的探望,让父亲有了太多的盼望,这是我的遗憾。曾经许诺开着车带着父亲在城里逛逛,已经无法实现了;曾经许诺让父亲到家里多住几天,更无法实现了。再多的鞭炮、礼花和锣鼓已无法换回父亲那鲜活的面容;抱着父亲的骨灰,即使穿越多么繁华的城市,多么美丽的风景对他而言,都毫无意义了。留给他的,只有一垺黄土;留给我的,却有太多遗憾。
愿父亲在地下安息!
湛波,男,汉族,中共党员,年10出生,贵州遵义人。自幼热爱文学,曾有一些小作品零星在刊物发表。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作家协会第一届主席,现为贵州省遵义市作家协会会员、常委,供职于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档案馆。
“我的父亲母亲”全国散文、诗歌有奖征文大赛征稿启事
为了让儿女们有机会表达对父母的感恩与或祝福,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早6点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