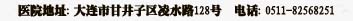(作者:东篱朗诵者:海俊)
我不想再看下去了,此刻,我最想知道的是姑姑和老小伙的情况。从我昏迷到清醒的这段时间,还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姑姑和老小伙的情况。
我预感到姑姑和老小伙的情况非常不好,要是医院来看我了。一想到老小伙,我又开始心慌,我觉得我的手脚莫名地抽动,无法停止。我被吓坏了,张梅梅更是吓得去叫医生。医生一来,我却又突然好了。有个护士被我折腾烦了,临走时嘟囔了一句,神经病。是的,从这个时候起,我的神经病的毛病已经在我的身体里疯狂地生长起来了。
我让张梅梅到我家里去看看,打问一下。她回来后告诉我说,家里没有人,房门紧锁。她使劲地敲门,把邻居的邵阿姨敲出来了。邵阿姨告诉她,那天警察来之后,叫来,医院,把被姑姑打伤的小医院。然后把姑姑和老小伙以及打上门来的另三个男人带到了派出所。
邵阿姨有个亲戚在公安局里,邵阿姨专门跑到亲戚家,拐弯抹角地打听到这个案子市上有个领导打了招呼,三个男人被放回去了,而姑姑和老小伙却一直被关在派出所的留置室里,没有放回家。被打伤的小伙已经请了律师,取了证,也请法医做了鉴定,光头受了伤,鉴定为轻伤,按法律规定,轻伤即构成犯罪,姑姑由此可能坐牢。派出所的人还到小区物业办以及邻居家里取了证,共有四个人证明看见姑姑拿铁棍打人,其中当然也包括邵阿姨,邵阿姨毫不隐晦地说看见姑姑打人,对着张梅梅又重复了一遍。说的非常具体,绘声绘色。
我的孩子,那个还不谙世事的小家伙,在6月22日那天,被另外的一群人抱走了。
这群人肯定也是赵虎派来的,他们抢走了我的孩子。
邵阿姨说,人家抱走孩子是对的,人家爷家才是正主,这孩子跟着神经病,早晚也会成为神经病的。
那天晚上,医院里,旁边的两个人是不是也睡着了,我不知道,这会不见那两个人哼哼唧唧了。我最讨厌的是挨着窗户住着的一个中年妇女。她因为打麻将不清钱和人发生争执,吵架,被人打伤,医院,伤情好像并不是很重,每天照吃照喝,大声吆喝,走来走去。不知道她伤在那,医院就是不走。最讨厌的就是她不停地打电话,给她的牌友,讲述她被打的经过和打麻将为什么不清钱的事,让那些牌友为她评理。
“她狗日的欠我多少次我都没说啥,我欠她一回狗日就不愿意。妈来个逼,能玩起就玩,玩不起就不玩,啥人嘛……”她不断地重复这样的话,令我耳朵生茧。我听见电话那边有人向着她,随声附和她,她便肆无忌惮地大笑,要是对方没有附和她,她便在电话里和人争吵,争吵自然也是肆无忌惮,医院里,非得说得对方承认她是对的才完。
中间床上住着的,是一位老太太,老太太一个人在家不慎摔了一跤,大腿摔掉下来,医院,一直在家躺着,正是七月流火的天气,很快感染了,眼看老太太头大如斗,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医院来。老太太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打针,不能滴的太快,白色的,酱色的,茶色的液体一滴滴象测定时间进程的滴漏一样沉重而缓慢地滴进老太太的身体里。但老太太的状况却在一天天迅速恶化,她的痛苦的呻吟一天天比一天地频繁而闷长。
医院的时候,她的肚子已经鼓涨起来了,脚也肿起来了,很明显,她很快就要死了。她的两个女儿坐在床头,非常平静地在聊天,对于她们的妈妈正在朝黄泉路上的行走安之若素,医生也很令人震惊地平静,过来按一下老人的腿,浮肿苍白毫无血色的腿立刻显出淡红的深坑,医生说了句,快了!转身便走了。医生按腿的动作并不是准备实施新的抢救,而是在判断还有几个时辰这位可怜的老太太就要结束在人世的旅程了。医生和老太太的女儿们都在等待着这个滴着吊瓶的人早早收场,结束这麻烦的一切。
终于等到了夜晚,说着麻将事的女人总算安静了下来,老太太的呻吟也更加的少气无力了。头顶上刺眼的两根长条灯被关掉了,只剩下床头上的小灯发着昏黄的光。医院的夜晚来临了。
医院的夜晚从来都不是安静的。医院了,每天晚上都能听到从走廊上传来的尖利叫声和那凄厉瘆人的哭声。一定是有人医院,或者,一定是有人抢救无效突然死掉,年迈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她们会发出一样悲怆无比的哭喊。哭声是那么令人震憾,那么令人胆寒,好多次我被这恐怖凄厉的一声长啸惊醒。紧接着是大夫、护士以及死者家属急促的脚步声在走廊上穿梭奔走。立刻从各个病房冲出去很多人到走廊上去看。
他们想知道,是怎样的一个人又死掉了,他是什么身份,多大年纪。很快,一辆白色的担架上一个白布蒙面蒙身的人被一群人护拥着推出了长长的走廊,消失在走廊的尽头。医院,也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从没有到走廊上去看过,我只蜷缩在病床上听那一声声撕肝裂胆的哭声,然后又是一片静寂。这静寂比起死亡的喧闹更加地令人恐怖。
那个爱唠叨的女人总是喜欢絮叨死去人的情状。
“他是被人杀死的,——他家是农村的,在‘大世界’当保安,听说刚干了不到一个月,——他很年轻,才二十多岁。送来晚了,血流干了。——他穿着白球鞋,鞋窠篓里都灌满了血。——”
这个讲着满口河南话的女人,讲起来没完没了,听起来她比警察掌握的还要细致。
每次她讲完之后,我便不能入睡,死去的人脸便清晰地在我眼前晃动,我虽没见过那死去的人,但却总能找到一个独一无二的面孔,真切又鲜活地出现在我眼前,这个人含着满脸的悲愤,张着口,向我讲述他被残忍杀害的经过。他的眼睛满含着泪水和祈求,口里冒着白气,希望我能写诉状替他申冤。我若是没有答应,他口里的白气便立刻就成了血水,象水管一样向我喷来。我立刻大叫一声用被子蒙上头。
我突然间大叫几次之后,河南籍的女人就向大夫反映我是精神病。大夫沉默不语,外科主任也来了好几次,一群白大褂围着我沉默不语,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是怎么看我。英俊的高大夫眼里总是饱含着同情又耐人寻味的目光,象是看待大街上被耍的猴子一样的眼光。
有一天半夜,我又尖利地大叫一声,鞋子也没有穿,就跑了出去。
我看到我的姑姑死了,她就躺在棺材里,棺材怎么是白色的,还没有来得及上漆就把姑姑放进去了,姑姑头上顶着花头巾,穿着带牡丹花的收腿裤,脚上穿着花花鞋。姑姑什么时候缠脚了,她怎么是个小脚女人呢,鼓鼓的,尖尖的脚象棕子一样。她的脸一片惨白,象洒了一层雪似的。她静静地躺在那里,象出土文物一样。有人在喊,赶快把盖子盖上,不要让这女人跑了,她是神经病。又有人喊,她不会跑,她在等她的女儿。她女儿来给她盖盖。
我光着脚跑到姑姑棺材前,扛起一块木板,要给姑姑盖上盖。怎么,我忽然看见,棺材里还躺着一个人,一个男人。他穿着一身整齐的中山装,蓝色的,还扎着领带。是那种出席重要场合的装束。可是,他却用胳膊紧紧地搂着姑姑,身子斜侧着,把好好的衣服都弄皱了。他怎么能这样呢,这是姑姑的棺材,不是他的,他怎么又粘着姑姑呢,这个男人,一辈子都在粘姑姑,死都要和姑姑死在一起吗?
我想把他拉起来,“咚”地一声,头却碰在了棺材上,我好疼,一下子坐在了地上。
医院走廊的门口,两扇玻璃门紧锁着,中间用一条粗铁链子挂着,我咣当咣当地推门,铁链子随之发出沉重的巨响。我推开了一条缝,够我的头钻进去,正如我小时候钻五号信箱学校的大铁门一样。我把头拱了进去。
“你在干什么?”
护士长在我身后大喝一声,一把从门缝里把我揪了出来。张护士长平日是那么和善,此刻粉红的圆脸却一脸怒气。她杏眼圆睁,一副恨不能立刻把我杀了的表情。又来了几个护士,她们七手八脚把我拖回了病房。
当我被安抚到床上之后,那个河南女人却又吵起来,说她坚决不能和神经病人在一起住。她腾地跳下床来,冲进医生办公室。值班的是年轻的小肖大夫,她咚咚地砸开了小肖大夫的门。
“要么她走,要么我走。”
她大喊大叫着,要求把我赶到其他病房。她是不舍得挪窝的。医院的人,挨着窗户的位置是专门留给她的。有宽大的窗台,可以放东西,还可以扒在窗台上望望窗外远处的教堂尖顶,和外面的绿树。还可以晒上太阳。靠门口的两张床来了家属和看客,也可以拉上隔帘不理不睬,求得一隅的安宁。
可是这咋咋唬唬的女人,争来这小好处,小利益,并没有好好享用,她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