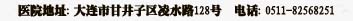白果熟了七十年代后期我在顺义前桑园插队。我们插队的形式有点特殊,不再像以前那样分配到村里的生产小队劳动,而是集中劳动、吃饭、宿舍、分配,叫做四集中,独立于村里的生产小队,时称知青队。村里用国家给的钱盖了知青宿舍,拨出了二百亩地,配了一挂大车。白海棠驾辕和拉套的两匹马是从内蒙古买来的。它们是母子俩,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土黄色的蒙古马,个头不大但很匀称,性情温和,从没有听到过它们嘶鸣,也没有见到它们尥过蹶子,乖乖的听着车把式的吆喝,默默的劳作。送粪、拉麦子、耙地、拉犁的活就靠它们了。黑枣时隔不久,母马被村里调换走了。这匹母马六七岁的口,正在生育期,换走是为了配种给生产队添丁进口。形影不离的母子俩终于分手了。不知道这对母子是否会伤心离别,即使知道,又能如何呢。总之母子俩就这么分开了。自此之后,很少再见到这匹母马了。直到分配回城,也不知道母马最后是否受孕了。留在知青队的儿马拉车时被车撞死了。海棠事情的原委大概是,知青队的这挂大车在马路运送东西,路过进村的路口时拉套的儿马以为是要回村了,于是向左转横跨马路,后面驶来的拖拉机猝不及防,把儿马撞倒了。有句话叫老马识途,真是一点不假,但儿马却被这识途给害了。那天偏偏不回村,若是老把式或许要吆喝两声,提醒牲口直行别拐弯,偏这天赶车的是位知青,还是不够老到。如果说从这件事情里体会到什么,就是经验这个东西是太重要了。花椒儿马伤的很重,一只后腿不能沾地,虽然没有外伤流血,但老农说内伤严重,已经废了,今后再也不能拉车犁地了。于是决定杀掉。牲口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为人劳作,做牛做马是得不到善终的。宰马的时候我没有去看,因为不忍。马肉大部分被村里分掉了,知青队只吃了一顿马肉包子。在几个月吃不到一次肉的时候,诱惑还是很大的,可眼前总是晃悠着儿马的样子,一口也吃不下去,给了别人,找了点别的东西糊弄了一下饥肠辘辘的肚子了事了。栾树果总觉得那天驾辕的不是母马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否则,亲眼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撞,太过残酷了。用母马交换来的是一头老骡子和一匹老马。如果不是老了,但就这头只骡子就值那两匹蒙古马,更不用说这匹枣红马了。人有人老珠黄之说,牲口亦如是。女贞果先说这头老骡子。这头老骡子个子不算小,该是头马骡,当年必是干活的好手,可惜如今只能给枣红马当梢子了。老骡子皮毛本是深棕色,因为太老,毛梢倒有些发白了。木瓜老骡子脾气特拧。有知青跨上骡背,想骑着骡子兜风,可老骡子原地站着就是不走,任凭怎么吆喝抽打,依旧纹丝不动,似乎早已拿定了主意,干活可以,玩,不伺候这口儿。这位知青无计可施,于是只好放弃。看来,遇事及时坚定的表明态度,也不失为应对的法子,叫做一拳敌得百拳开。从此,知青们再也无人动骑老骡子的心思。蜂蛾与醉鱼草再说这匹老马。老马浑身枣红色,身材高大。老农们讲起了这匹枣红马都赞不绝口,说它年轻的时候,一是身大力不亏,干活倍有劲儿。二是聪明,碰到车陷泥坑或沟坎里了,车把式根本不用轰它,只吆喝牵头拉套的牲口就行,只要前头的牲口弓腿使劲了,枣红马才借机发力,两股劲合成一股劲,从陷坑中脱出也就容易了。就是到知青队的时候,枣红马看上去也依旧是器宇轩昂,威风凛凛,惹人喜爱。瓢虫与喇叭花枣红马和人特亲近,每次我走近马棚到牲口槽子那儿,枣红马便会主动凑过来让我抚摸。枣红马一直受宠,也就知道了求撸。谁想骑乘,枣红马来者不拒。有一次一个知青把枣红马骑出去,没想到枣红马摔倒了,这位知青的腿严重挫伤,休养了好长时间才痊愈。知青队还有头小毛驴,青灰色的皮毛,大约也是因为年岁大了发配到知青队了,没记得有什么正经的差事叫它做。紫藤小毛驴的脾气秉性和老骡子老马都不同。它知道用犯坏来对付欺负自己的人。遇到想骑驴的人,它既不敢像老骡子那样干脆拒绝,也不像枣红马那样欣然接受。先是躲来躲去,等到挨了鞭子,不得已叫人骑了上去,走起来便趔趄着向树上或电线杆上蹭去,叫你骑不成。惹毛了骑驴的人,难免要挨揍。等到下次见到了打过它的人,先自浑身打哆嗦,躲到连牲口棚的角落里。骑过这头毛驴的人里面也曾有我一个。紫李负责喂牲口的大爷个子不高,说话慢条斯理的。有一次问起他老骡子老马还能干多久,他说,牲口老了,牙口就差了,但若是精心点,把草料轧细点儿,牲口还是能多干几年活儿,人也是一样。不幸的老骡子和老马终于摊上了一份累活苦活。松塔七十年代我插队的前桑园村农民的收入可怜,村里富裕的的小队一个劳动力的日工分是四毛多钱,穷的小队每日工分只有二毛八分钱。拉沙子卖到北京城区的建筑工地是个来钱的路子。一手扶拖拉机车斗的沙子六块钱,一马车拉的沙子还要多些。从村西六里地远的板桥村装上沙子,然后拉到和平里附近的工地。桑椹冬天的时候,早上五六点天还黑着,就要套上车赶到板桥装沙子,然后奔城里。那会儿还没有京承高速,大致的路径是要走掉头经过北郎中、赵全营到牛栏山,然后一路向西南方向经孙河,往返一趟大约一百华里。在知青队做饭的老马山主动揽下这份活计。年近六十的老马山平常有些气短,说起话来嗓子里有些拉风箱。我担心老马山的身子骨是否顶的下来,于是和队长说起,队长没有做声。萱草老骡子老马加上老马山,三个老东西数九寒冬奔波在路上。老马山冷的不行了便下车走一段然后再坐上去。车重牲口老,从去到回,慢腾腾的至少要十多个小时才能回到家。没走几趟,老马山肺气肿犯了,人便卧床了,一个冬天也没有治好。一趟活的补贴是一块钱。就这一块钱,差点要了马山的老命。晨记晨记(图片均为本人拍摄)过往文章链接老书记孙维岳---插队记事之一陈年旧事--插队时的回家路重聚石经山记窗外有鸟鸣戊戌泰山游记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转载请注明:http://www.pdnns.com/ways/117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