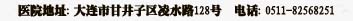专家简介
王杨周,女,年2月生,山西省沁水县人,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硕士研究生学位。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年7月毕业于长治医学院,年在职取得硕士研究生学位。年9月至年1月,在长医院工作。年2月至今,在医院重症医学科工作。年9月至年9医院重症医学科进修学习,获得优秀进修生嘉奖。平素工作认真负责,技术精湛。年曾作为一线医师参加手足口病流行疫情救治工作。年,作为山西援鄂第一批医疗队员之一,医院感染科重症病区工作。随队负责当地新冠肺炎确诊及危重病例救治工作。工作中,她尽职尽责,恪尽职守,关心病患,关爱同事,得到同事及患者的认可。玻璃窗的那一边
——新冠肺炎重症病房里发生的故事
我来自医院重症医学科,是一名重症专业的医生。此次新冠肺炎的疫情中,有幸作为山西省第一批援鄂的医疗队员到湖北省仙桃市做医疗支援,使我能够直面疫情,切身体会到了一个强大的祖国和团结的人民带给我们的安全感,并在58天后顺利完成任务,安全返回。此行经历了我职业生涯很多的第一次,也经历了我人生中很多的第一次,收获了很多感动,今天借这个平台,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历。
今年年初新冠爆发时,和很多人一样,我最先想到的也是当年的SARS,年,我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只记得那时我们山西,太原是重灾区,很多医务人员和学生被感染。我有很多同学在太原念大学,被封校了,回不来,他们说有全副武装的武警看守学校,发热的同学,会被穿着防护服的人接去隔离,我也亲眼见过有同学被那样接走,那时大家都是怕的,隔着电话,我都能感觉得到他们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气氛。有的人被接走了,就再也没回来。但我是医学生,我有老师报名支援SARS,虽然最终没去成,但当时,我体会不到他们怎么想到要去冒这个险,当然,我也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大好青年,该有的思想觉悟还有,那时心里还真有些佩服他们。
年汶川地震时,我已经走上工作岗位2年多了,算是一个吃苦耐劳有理想有抱负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大好青年,每天就是开开心心上班,乐乐呵呵下班,美滋滋抱着电脑查查资料,那一年,我在救治小儿手足口疫情的一线,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病人和伤员经历着什么,但是灾区的惨状同样不是我能想象的。那一年,虽然自己没资格报名,但有熟悉的前辈同事报名支援汶川,对他们我是又羡慕又佩服,羡慕他们可以去实现救死扶伤的伟大理想,佩服他们有能力去灾区救援,为他们送行时,我是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两眼冒着星星送他们走的,那时我想,他们的眼泪大概是感动吧,但看着大巴走远,不知怎么的就想到电视上的灾区,伤员,余震,泥石流,道路坍塌等等场景,我突然就兴奋不起来了,我不知道除了辛苦点儿工作之外,还有什么在等着他们。你能想象吗?一个傻兮兮站着的姑娘,脸上花痴一样的笑还没有收回来,就不知不觉泪流满面,那一刻我突然就感觉到那辆大巴把我和灾难隔离开来,越行越远,电视上那些危险都走不到我身边,我觉得他们是那么高大,我想像他们一样。两年后,我进入到重症医学科,每天的工作就是抢救,抢救,直面生或死,经历过重大事故,经历过甲流,看到过绝望,也见证过重生。十年以后的今天,我早已不是当年空有一肚子理论和一腔抱负的“大好青年”,我可以坐下来冷静的比较新冠与SARS/MERS,听听专家的分析,查阅人类流行病大爆发的历史资料,自己心里对新冠的传染性/致病性和致死致残的风险也是有大概的猜测的。预备队报名时倒也没有什么高大上的动机,实在是专业对口,不报名觉得对不起自己这么多年辛苦练就的技术和经验,对不起那年傻傻杵在大巴后面又笑又哭的自己。1月23日武汉封城,那时我就有了思想准备,我是在大年初一晚上接到的通知,说实话,没犹豫,但是也想过,万一感染了,万一回不来,心里已经把后事都想好了,只是担心家人担心我,没像有的队友一样,留了遗书出发。医院所有院领导都亲临为我们做准备,带了一周用量的口罩,防护服,手套,帽子,护目镜,面屏,消毒剂,工作服,雨鞋,还有备用药等等,想到什么就马上解决什么,我记得随身手消毒剂,护目镜和防护面屏是把全院的储备都给我们几个带上了。不知道几时出发,不知道支援哪里,不知道去多久,可第二天一早,我走得很放心,我知道,医院是傾全院之力在为我们做后盾。
出发时,我所支援的仙桃市确诊病例还是个位数,潜江和天门还是0。一路会合各地队员,从我们4人到人,气势越来越壮大,从太原出发,夜里到达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空荡荡的机场,只有我们,之后,我们兵分三路,分别向仙桃/潜江和天门出发,深夜的公路上只剩这一辆大巴,沿途设有关卡,车灯照亮了数名值班人员,他们向我们致敬,然后放行,车灯走远了,他们也渐渐消失在黑暗中,这是我和封了城的武汉的第一次接触。
2天后,我们完成了培训,分好组,做好防护准备,做好与当地的交接,队长原主任他们按照流程进出了2次病房,补全了设备,理顺了流程后,确保了安全,才让我们分组第一次进入病房。理所当然,我分在重症组,还有一个上级医生带着我,医院的王秀哲主任,之后我们“大王小王”组合和其他6名医生,30名护士,开始了为期58天的合作。本以为开始的工作会比较轻松,可没料到疫情远不是个位数的确诊人数表现出的那样,防护服对我们的影响也不仅仅是一件衣服。发热门诊人数激增,确诊人数蹦着跳着往上涨,医院又增加了2所,而当地的医护已经一人当好几个使,连轴转了二十多天。我医院的重症病区,第一天上班,就接收了30个新病人,病区有了4个重症病人,第二天8个重病人,第三天10个......工作量比预计增加得更快,稍微动作大点,就喘不上气,而医生查房还要同时和病人聊聊天,他们都很紧张,许多病人全家都被隔离了,饭有专人统一送,但是个人用品就不一定还有人可以往病房送了,杨主任组为患者带来了自己备用的牙刷,保温杯,张主任和段医生为患者开了中药,煎好,送进来,郭主任带着小杨为需要的患者做床旁超声,我们和当地的刘主任一起,边查房,调整呼吸机,边要负责为乏力的患者喂喂饭,有时要补充营养液,帮忙翻个身,整下衣服被褥什么的。回去还要做总结,治疗还需完善,忙碌中时间过得飞快。
在这里,每天穿的防护服,带的口罩手套都不一样,有很多人主动联系捐赠,我的同学和朋友们也都想通过我尽一份力,我不知道今天使用的防护用品是哪个组织或个人捐助的,明天又是哪个,反正我相信在这里我总能得到尽可能好的防护,医院,这里的上级,以及社会各界。每次进病房时,“大王”都得看着我这个“小王”穿防护服,确保合格,一起进病房,出隔离区时,“大王”总是让“小王”先出,盯着“小王”每一步都安全完成后才自己出来。看,我的后盾和保护者就是这么强大,无处不在。
这一天,收到一个特殊病人,来自武汉市区,全家确诊,家庭中已经失去了2名亲人,他的妻子和儿子,我在交接班汇报表上在他的名字旁,用红色粗体标了“高危”二字。半个月后,山西第二批支援队员到达仙桃,人员得到补充的我们完全接管了整个重症病区,现在,轮到“小王”看着新人穿脱防护服了,他们说“小王”也很让人安心,那是啊,“小王”是被保护着锻炼出来的,自带保护气质。而这个“高危”的病人“吴爹爹”,换成普通话就是“吴大叔”,归我们“大小王”组管。“今天气够用吗?”我每天查房都得要隔着防护服大声喊,他常常会回答“吃过了,吃不了多少,没有胃口”之类,反正总是听岔。每次都得一个一个字连吼带比划,才能让吴叔理解我说什么,“还是不够,还是胸闷得厉害,你们要给我用最好的药啊,我求求你们了,我老婆没了,儿子也没了,我得活下来照顾孙子啊......”说着说着他眼眶就又红了。他有呼吸困难,情绪不稳定,吃饭不好,不用强效镇静药几乎完全不睡觉,病情进展很快,能不能扛过去,谁也没把握。而因为新冠肺炎已经失去的2名亲人,每天查房他都要重复这样的车轱辘话,向每一个医生护士一遍遍倾诉。他焦虑,他恐惧,还在隔离中的孙子让他有无比强烈的求生欲。几天下来,“大王”带着我,我们连听带猜已经基本能听懂他的仙桃普通话,吴叔对我们每天问什么也能猜出个七七八八,配合着手势,查房终于不用带翻译了。
每次磕磕绊绊了解完病情,听完他又一遍哭诉,安抚之后还得反复叮嘱“绝对不能下床了啊”,他会说“知道了,不下床,可是要护士小姑娘们喂饭,帮忙大小便还是不好意思啊”,但是这样的肺功能,下床可是在拿面子搏命,我们只得继续安抚,磨半天嘴皮子,才能让他不情不愿的答应下来。
查房最后的程序,指导握手锻炼和踝泵运动,以增强免疫力,防止下肢血栓并发症:“躺在床上一定要动动手脚,跟我学,两只手虎口合在一起,交握住”,我得边喊边示范,“我不渴,不喝水”,吴叔还是会听错,不过几天下来的习惯告诉他,跟着我做:握手,揉搓大鱼际,揉热了,换手。边反复做,边聊,聊了吴叔作为一个湖北人居然不吃辣椒,聊了我怎么样用热水一遍遍涮了菜吃,什么菜怎么涮都仍然是辣的。成,今天做的比昨天强多了,能转移注意力到运动上来,总是好现象。继续,踝泵运动,“勾脚尖,使劲,停住,好,1,2,3,别松”,上手用力扶住他的脚尖,“坚持住4,5......10,非常好,脚尖压下来,使劲,停住,好,1,2,3......”,掰着脚尖维持10秒,再勾起,再压下,然后以踝关节为轴心转脚尖,终于结束,短短十余分钟,防护服里,我已是一身大汗,护目镜上的雾汽模糊了视野,水滴沿着眼镜流到嘴里,是咸咸的味道,观察下吴叔的呼吸,隔着水线趴到监护仪上看看,嗯,这个运动量病人可以耐受。“每天要做五六遍啊!”,我得再次大声嘱咐。“知道!我没事就做!”这次吴叔可算听懂了。
随着语言障碍被克服,学会“动手动脚”的病人越来越多,新老患者互相传授,教授程序也变得相对容易。十几天过去,吴叔从起不了床,到习惯了护士喂饭·帮助大小便,到戴上呼吸机,再到撤离呼吸机,除了昏迷的那两天,每次进去查房都讲讲新冠是什么东西,聊聊吃喝,送点奶和营养粉,聊聊睡觉,聊聊山西,聊聊武大的樱花和吴叔的孙子,再动动手脚。吴叔精神好转了,指标好转了,饭能自己吃了,晚上能睡几个小时了。查房时,他能隔着防护服认出治疗组的“大王”“小王”和每一个医生,记得送过营养粉,帮忙活动手脚的医生,记得哪个医生轮休了几天,记得哪个护士喂饭总是很温柔,见到我他就自觉握手,做踝泵,邀功似的告诉我昨天做了好多次。命终于是捞回来了!
这天,隔壁6床住进来一个危重的奶奶,大口大口喘着气,操着一口不普通的“仙普”,断断续续与我们鸡同鸭讲地交流病情,“大王”教授带着我们几个,各种口音连说带比划着也说不清时,吴叔就自觉充当了我们的翻译,6床奶奶不愿带监护仪,坚持下地大小便时,吴叔现身说法帮我们劝服了她,教授握手及踝泵运动时,吴叔给她做示范,“动手......动脚......”。后来,6床奶奶也戴了呼吸机,再摘掉呼吸机,坐起来,一路走来,5床的吴叔尽职尽责完成好了他“助理医师”的职责,他负责翻译,示范,劝慰,能做的都帮忙做。全国人民都窝在家静止了一个多月,在我们的病区,5床恢复了,6床恢复了,30床出院了,12床恢复了......玻璃窗里的人,进进出出,吴叔和6床奶奶在我们撤离的当天下午出院,如愿以偿带着他心心念念的山西中药,我到底没能亲自送他们,然而我也永远不会忘记重症病房里的这位“助理医师”,还有其他病房无数的“吴叔”,无论如何,希望大家能各自安好。
返程那天,当地的战友来了不少为我们送行,有交警开道护送,仙桃市民从市政府一直到高速口,夹道欢送,我终于第一次放任自己哭了出来,我从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可以承担起这样的深情厚谊和礼遇。这次是白天,经高速驶向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这次一样要过关卡,依然有工作人员敬礼致敬,不过这次我能看清他们的脸,回以我们的敬意。
短短58天的经历,是无数家庭的破碎和重生,后来,我们还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