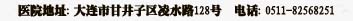问:我也是煤矿人,怎么加入组织?
答:点击上方蓝色“煤矿安全网”!
亲爱的矿工兄弟们,我们推出了专题《矿工兄弟,辛苦啦!》专题,详情点击文章底部左下角“阅读原文”,精彩不要错过哦!底部也可以评论啦!您可以参与互动哦!
尊敬的龚文密市长:
我是邵阳市短皮桥煤矿老矿工的儿子,一个在读博士生。在红网上看到龚市长热心网络,关心民情,深受鼓舞。故想替我那个弥留之际的父亲和矿里面11个肺病晚期的老矿工给市长先生写一封公开信,讲一讲老矿工们的故事,尤其是问一问市长先生,他们,真的该被遗忘吗?为什么在煤矿辛苦工作了20、30年,连最后的工伤鉴定机会都得不到吗?
写这封信是因为前天接到家里人的电话,父亲快要不行了,是继续插管还是放弃治疗?继续插管请继续缴费,放弃治疗请准备后事。这对我来说是个艰难的决定。他们知道,一个博士生没有能力去承受高昂的医疗费,而他们也为父亲治病尽到了自己该尽的义务。哥哥对我说,今天他和几个老工人又去邵阳市劳保办问了,说父亲所在的国有煤矿早改制了,父亲作为“内退”(下岗的另一种说法)员工,没有人来负责工伤鉴定了。矿里几个像父亲一样的老煤矿工人再次被制度遗忘了,意味着他们几十年的工伤仅仅因为一个单位的改制,而不被得到承认。我问,凭什么在矿井下工作了20多年,患了的哮喘、呼吸衰竭、肺气肿就不能有个工伤鉴定呢?哥哥回答说,办事的人说,这么多年了,谁知道你的病是不是在别的地方得的?
此刻,我觉得自己很没用,因为尽管自己已经尽全力来读书,争取出人头地,并且从本科开始就靠自己做家教和打工养活自己,读研之后每年也为父亲母亲治病提供了几万块钱每年的治疗费,但博士的光环无法给我足够的经济实力去独立支撑父亲的继续治疗。我羡慕嫉妒恨,那些近期在中国股市中赚的朋满钵满的人,我一没资金二没胆量三没技术,所以无法靠炒股赚大笔的钱来给父亲继续治病。这一刻,我明白了上海博士生所说的“知识无力感”。
此刻,我很愤怒,因为父亲这一群体被遗忘了。一个号称为工人阶级的一群人、一种标志着下岗工人的集体,一个号称为最为先进的“工人阶级”,曾经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奉献了青春和健康,他们曾经的骄傲和自傲,他们为中国改革所做的巨大牺牲和付出的巨大成本。然而,临到晚年,他们挣扎在病痛和贫困之中,却因为原来工作的单位“改制”、破产了,下岗了,却连起码的工伤鉴定机会都得不到?国企改革已经让他们受伤一次了,好吧,谁叫他们是最为先进的工人阶级,那就奉献一次吧。改革30多年,国家有钱了,经济发展了,为什么连起码的工伤鉴定都得不到承认?为什么不承认他们的工伤?为了不被忘却,我这个知识无力的博士生,写下这些文字,算是对父亲、对很多像父亲这样的矿工,对那个被遗忘的群体,留作纪念吧。
父亲是国有企业邵阳市短陂桥煤矿工人,年到那里参加工作,一干就是20多年,直到国企改革被下岗。对于父亲的所有回忆,都跟那口黑呼呼的矿井有关。我是小学四年级跟随父亲住到煤矿里的,那时,母亲还留在农村。我一个人在父亲上班时总有点怕怕,所以都会跑到矿井边等父亲下班。下午三点多时,铃声一响,一辆黑色的矿车拉上来一大队人,他们从那口黝黑黝黑的矿井中走出来时,全身上下除了眼睛没有一处不是黑呼呼,所以根本认不出谁是谁来,这时,总有很多叔叔在我脸上抹上一块煤灰,以此取笑我,而父亲一见到我,就会对守在矿井边等待的我露出洁白的牙齿微笑。哦,于是我在黑呼呼的人群中,认出了父亲,向他跑去。。。。。随后,大家一起奔向集体澡堂,澡堂水很大,哗哗的黑水从澡堂奔涌而出,在热水的冲洗下矿工人恢复了活力,回到了人间,于是在那狂欢般的大笑中,呼吸道疾病早已经盯上了这一人群。
矿工生活总是有莫名的恐惧,以至于很多年后我读到《平凡的世界》时十分佩服孙少安去做矿工的那份勇气,也深深懂得他师傅的故事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因为事故,总是与煤矿生产相伴相随。在我记忆中,有太多这种恐怖的故事了,瓦斯爆炸、塌方、冒顶,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词语。总是在某个清晨,突然听到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声和吵闹声,然后大家一齐奔向矿井,看看谁上来了,谁没有上来。看到自己老公上来的,那女人又哭又笑,而迟迟不上来的,则是绷紧了神经担忧,焦急地看着下一个上来的人。最后,一直不见上来的,就会发出撕心裂肺的痛苦,边上的人既同情她又庆幸幸亏是她而不是自己。在我记忆中,有很多个叔叔、伯伯,前一天还在我家喝酒吃饭打扑克,第二天就再也见不到了。他们的老婆就拿了点抚恤金,然后到砖厂去干活了,而他们的子女,就每天拖着长长的鼻涕,衣冠不整,无人看管了。
印象很深的,有几个叔叔,一个叔叔听说我考上了大学,很慷慨地给了我块钱,我一直十分感激。后来听说他也在一次事故中死了。关于他,矿里有很多传言,带点恐怖色彩。几年前,他的同胞弟弟,就在一次事故中死了。而他已经成了生产队长,肌肉很发达,挖煤很卖力,据说每月可以赚块钱,那时日子活得倒也红火。那天是他弟弟忌日,朋友说你别去上班了,今天是你弟弟的忌日。他说,我再上一班吧,大儿子明年上初中了,要钱用。结果,他这一去,就遇上了冒顶。父亲对我说过,他的大腿被压住了,动弹不得,他哭着对救援人员说:“帮帮忙,再使点力啊,我还有两个儿子没长大哪!”但救援人员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好多年后听说,他家很惨,老婆改嫁了,大儿子神经有点问题,小儿子读书不行,就学会了在网上偷游戏工具卖钱养家。一开始还能养着哥哥,后来不知道怎么染上了吸毒,每天吃一顿没一顿的。前年回去见到过他老婆回来办低保,我帮她写了分申请书,她很感激的样子。其实,我很心疼,因为,我能为他们做的不多,而她的老公,那个肌肉发达、大方慷慨的煤矿工人,怕是被人永远地遗忘了。。。。。。
还有一个叔叔,讲话时总是带一句口头禅“这个暖子”,所以后来大家都忘记了他的名字,干脆叫他“这个暖子”。他总喜欢开玩笑,所以大家都喜欢他。但他特别小气,打扑克时输了几块钱就心疼,但又喜欢打。因为家里在农村,他很扣,时不时到我家来蹭饭吃。有一天,他难得地买了一条鱼到我家一齐吃饭。然后打牌时,手气竟然特别好,一连赢了几十块。我至今记得他赢钱时两眼放光的那个场景,嘴笑得合不拢了。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农村婆娘哭着来矿里了,大家才知道他家里有个生病的女儿很需要钱,而先天大牌手气大好,这叫“发死财”。现在,他也被遗忘了。。。。。。
后来,据说国有企业改制是大势所趋,煤矿效益不好了,厂里要改制,好多煤矿工人下岗了。45岁(50岁)以上的全部“内退”,内退的话每个月、块生活补贴。我记得,刘欢那首“从头再来”的歌曲在矿里播了又播。那首歌唱的很煽情,但我很讨厌,因为总是勾起很多不愉快的经历。因为就因为那次下岗,邻居家和我们家变得很穷很穷了。一个初中同学,因为母亲身体不好,不久就辍学了,家里太穷,她就来我家求我母亲带她去打工。我们时而听到邵阳汽制厂等企业里,很多家穷得要死,连饭也吃不上的传闻。而恰恰这时,父亲他们的哮喘病开始发作了,我们的家境也越来越穷了。而在企业改制、下岗的过程中,内退员工只能拿到多块基本的生活补贴,没有人想到,也根本没有人处理工伤鉴定的事情。母亲只能外出打工去赚钱养家,给父亲治病。我依稀记得,0年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但我决计不去读了,挣钱养家糊口。为了了个心愿,我一个人去学校看了看,想知道大学究竟是怎样的。我记得自己一个人在来到湘江边,望着滔滔的湘江水,我坐了一个晚上。。。。。。然后去到学校分给我的宿舍,在里面呆了一个小时,这样,我也算进了大学吧。第二天,背着包回家,准备去打工。母亲哭着说,人家孩子能读大学,我们再苦再累也要送。于是,父亲和母亲双双去邵东帮亲戚煮饭,逼着我去上大学。期间,父亲哮喘总是不断发作,但他总是买点普通药自己克服。
熬过了很多年,终于有一天父亲这一批人熬到了正式退休的年纪。父亲他们联合了煤矿里面同样哮喘严重的工人向煤炭局、社保处要求鉴定工伤,都每次都被各种理由拒绝了:要么找不到人来办,要么说这么多年的事情谁记得,更为恶劣的就是说谁知道这些年你在哪里打工得了尘肺病?父亲年纪越大,住院就更为频繁。9年和,先后两次带父亲医院(钟南山所在的呼吸研究所)看病,医生看了肺部x片结果说,肺部功能极差,纤维厉害,颜色为黑,跟20多年的煤矿生活直接相关,明显就是矽肺,你们单位怎么不算工伤呢?父亲无奈地说:单位没有人管这事,政府部门也没有人理。于是,年复一年,检查单、医疗费越积越厚,而肺部功能也越来越差,终于到了这么一个时刻。。。。。。
回到邵阳家里,才知道跟父亲同样处境的人很多,就现在还活着的,数得出名字的就有11人。去年去世的一个叔叔,走一步路都气踹如牛。他曾经拼尽全部家产去洗了一次肺,据说好了1个月,我还记得他很得意地跟父亲交流自己的经验,怂恿父亲也试试,但后来就突然记性呼吸衰竭去世了。呼吸衰竭是一个时不时就发作的病,很多家里条件不好的职工,就买点氨茶碱勉强维持。厂里就那么个地方,到处可以听到大声的咳嗽声和气踹声。
记得有一年回家,我跑到矿井去看过,那个巨大的黑洞,拉出来一车车黑色的黄金。父亲说,矿里在改制之后,承包煤矿的人都发达成千万乃至亿万富翁了,据说后来挖煤的人工资也涨到一个月了。父亲叹气说,可惜老了,挖不动了。然后是剧烈的咳嗽。我知道父亲很伤感,他的青春、他的力气、他的汗水,全给了那个黑洞,然后得到的是一个困扰他一辈子的尘肺和哮喘。是的,那个腰包鼓鼓的承包头是不会记得这群矿工的,那么,政府也忘记了么?
家里还摆着父亲年轻工作时“先进党员”、“先进生产工作者”的奖杯,衣柜里还可以翻出当时唯一的劳保品“口罩”,一副父亲受表彰的发黄的老照片还挂在墙上,这些东西在记忆着那一代最为先进的“工人阶级”的荣耀和付出。然而,如今这一切都被忘记了。难道,真的要像网上那样“开胸验肺”?然而,他们连开胸验肺的机会都得不到。
医院,奄奄一息,我还得做那个最艰难的决定。在矿里,还有11个矿工依然在跟病魔做着最后的抗争,他们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仍然提醒我们一段过去的岁月,一个被房地产、股票市场、酒吧和高速公路逐渐遗忘的群体。岁月像把杀猪刀,一个煤矿工人,数千万国企下岗员工,一代工人阶级,好似全被那黑黑的矿井吸了进去。很多年后,还有人记得他们吗?现代化的狂飙突进,商品房如雨后春笋的涌现,股票市场一掷千金的疯狂,高速公路的纵横交错。他们,争也争了,闹也闹了,最后只能认命了。
一种制度倘若没有良心,是不会想着去纠正什么的。而在网上,又太多诉求、太多希望解决的悲剧,他们这些矿工,似乎也不是最惨的。认命吧。
作为一个矿工的儿子,此刻写下这些文字,全当是最后的纪念吧。我没有更大的能力,只能在网上发出你们的呼吁,作为曾经最先进的工人阶级,作为国有企业下岗工人,作为为煤炭能源付出过全部青春和健康的矿工,我们不要施舍,不要救济,而只想要回我们基本权益的工伤鉴定。因为,这固然是一种伤痛,也是一种荣耀,这是我们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作出过贡献的一种承认,是他们那渺小的生活存活于这个世界的一种证明。
随着父亲他们的逝去,还有没有人来反思这种得不到承认的不公和痛苦。。。。。。。
龚市长,一个普通老百姓将这些文字写下来,希望您还记得,曾经有这么这群可敬更可怜的矿工们。他们的名字是:刘富清、尹伯清、徐喜生、周再喜。。。。。。(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