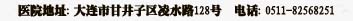对于“这本书的出版”“春天的到来”“她的走”和“长城的伟大”“柠檬的酸”这样一类“名词+的+谓词”(NP+的+VP)的结构(这里的“谓词”包括动词、形容词),汉语语法学界都认为这是名词性偏正结构。曾有一段时间,这类结构引起了汉语语法学界的热烈讨论。讨论的焦点有两个:一是这些结构里的“出版”“到来”“走”和“伟大”“酸”仍然是动词/形容词呢,还是名词化了;二是这类结构是否跟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在《语言论》(页)里所提出的向心结构(endocentricconstruction)的理论相悖。意见并不一致,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布氏的理论无需修改,这类结构里的“出版”“到来”“走”和“伟大”“酸”已经名词化了(即所谓动词、形容词名词化)。第二种意见认为,这类结构里的“出版”“到来”“走”和“伟大”“酸”仍是谓词,不存在“名词化”的问题,布氏的理论需修改。第三种意见认为,这类结构里的“出版”“到来”“走”和“伟大”“酸”仍是谓词,布氏的理论也无需修改;而所以会出现这种似乎矛盾的现象,是由于存在着“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的错综对应关系以及名词、谓词和主语、谓语跟指称、陈述的错综对应关系”的缘故。上述三种意见都缺乏解释力和说服力。第一种意见,说这种偏正结构里的谓词名词化了,其理由是,那谓词不能再带“体貌成分”、不能再带补语、宾语,因此谓词性减弱了。这种看法是站不住的。作为某一类词里的某个具体的词,它当然会具有它所属词类的各种语法功能,但当它进入某个具体的语法位置后,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它具有它所属词类的所有语法功能。譬如一个及物动词(如“吃”),它一旦带上补语后(如“吃快了”“吃得很饱”“吃不完”等),就不可能再带上宾语,不可能是再带上“了、着、过”一类体貌成分,不可能再重叠,它本身不可能再直接受“不”的修饰,等等。我们能据此认为那带补语的及物动词(如“吃”)改变词性了吗?事实上,在现代汉语中,即使像“春天的到来”这种结构里的“到来”的情况也不少见。例如,“所看的”、“所做的”里的“看”、“做”同样不能再带体貌成分,不能再带补语、宾语,不能再重叠,可是没有人认为其中的“看”、“做”的谓词性减弱了,更没有人认为其中的“看”、“做”名词化了。第二种意见,它对第一种意见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不好解释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中心语是谓词性的,而整个偏正结构会呈现体词性?整个结构的体词性由什么决定的?如果我们把整个结构的体词性说成是由偏正格式造成的,那么将会陷入循环论证之中。此外,说布氏的理论要修改,这要有足够的语言事实为根据,光凭汉语“这本书的出版”、“春天的到来”、“她的走”和“长城的伟大”、“柠檬的酸”这类结构的情况还不足以动摇布氏理论,如果硬要根据上述结构的情况对布氏理论进行修改,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将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第三种意见难以自圆其说,这里就不细分析了。我们觉得,不妨可以另作思考,具体说可以运用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形式语法学理论中的“中心词”理论(HeadTheory),来对这类结构进行再分析,再认识。形式语法学理论中的“中心词”理论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中心词”移位理论,二是“中心词”构建理论。这里只扼要介绍“中心词”构建理论。“中心词”构建理论,其核心观点是:有一个短语结构XP,如果其中所含的句法成分X的语法特性决定了整个XP的语法特性,那么X就被看作是XP的中心语,因为中心语的语类特点会渗透到其所在的母节点XP。因此,当我们知道某一个中心语能使母节点具有名词性语类的语法特点(标记为[+N]),那么就可推知,其所在的母节点一定属于名词性语类([+N])。这就是中心语的渗透性原则(PercolationPrinciple)。可见,“中心词”理论里的“中心词”,跟传统语法学里所说的“中心语”不是一个概念,也跟布龙菲尔德的“向心结构”理论里的“中心词”不是一个概念。传统汉语语法学里的“中心语”是指修饰性偏正结构里受修饰语(定语或状语)修饰的那个句法成分。譬如,“高大的建筑物”“慢慢儿说”里的“建筑物”和“说”就是中心语。显然,这里的“中心语”是跟修饰语(或定语,或状语)相对的。布龙菲尔德“中心词”理论里的“中心词”,是指包含在某个句法结构里、决定整个句法结构语法性质且与整个句法结构的语法功能基本一致的那个成分。按此理论,不仅上面所举的“高大的建筑物”“慢慢儿说”都属于向心结构,像“讲故事”“说完(了)”也属于向心结构。此外,还存在与“向心结构”相对的“离心结构”。譬如,“吃的”“红的”和“木头似的”这些一般所说的助词结构,就属于离心结构,因为像“吃的”“红的”是名词性“的”字结构,这种结构整体的语法功能既与“吃”(动词性)、“红”(形容词性)不相一致,也与助词“的”不相一致;同样,像“木头似的”是谓词性的整个结构的语法功能既不同于名词“木头”,也不同于助词“似的”。按此理解的“中心词”,其范围显然要比传统句法学里的与修饰语相对的“中心语”范围要大;向心结构理论里所说的“中心词”与传统句法学里所说的跟修饰语相对的“中心语”显然不一样。乔姆斯基生成语法学理论中的所谓“中心词”则是指某种结构中与之共现的其他成分都从属于(subordinate)它,并且整个结构的语法性质就由它所决定的那个成分。或者简单地说,在某个句法结构中的某个组成成分决定了该句法结构的语法特性,那么该组成成分就是该句法结构的中心词。按此理解的“中心词”,不仅与传统句法学里所说的“中心语”不一样,也与“向心结构”理论里所说的“中心词”不一样。这可分以下三点来理解。第一,有相当多的在传统句法学里所说的与修饰语相对的“中心语”以及在布龙菲尔德“中心词”理论里所说的“中心词”,如上面举的“高大的建筑物”、“慢慢儿说”、“讲故事”里的“建筑物”“说”“讲”,按乔姆斯基“中心词”理论也看作“中心词”。第二,“向心结构”理论里的所谓“离心结构”,譬如“吃的”“红的”那样的“的”字结构,按乔姆斯基“中心词”理论,汉语的“的”字结构也有“中心词”。那中心词就是“的”。这个“的”后附在某个实词性词语之后使整个结构具有名词性。这一点,朱德熙先生早就论证过,所以说这个“的”“是名词性单位的后附成分”;“的”字结构之所以具有名词性,就是由这个“的”决定的。第三,某些句法结构,如“三个苹果”“五条狗”“两张桌子”“八把椅子”等,按传统句法学,都视为“定—中”偏正结构,“中心语”分别是“苹果”“狗”“桌子”“椅子”;按布龙菲尔德“向心结构”理论,也将“苹果”“狗”“桌子”“椅子”看作这些句法结构的“中心词”。可是,按乔姆斯基“中心词”理论,认为这些句法结构的“中心词”分别是前面的数量词“三个”“五条”“两张”“八把”,而不是“苹果”“狗”“桌子”“椅子”。为什么?因为“三个苹果”“五条狗”“两张桌子”“八把椅子”这些句法结构都属于具有“量项”(quantifier/quantification,也称为“量词”)语法特性的“量化短语”,而这种“量项”特性是由“三个”“五条”“两张”“八把”传递和决定的。现在,我们按照上述乔姆斯基的“中心词”理论,来考虑、分析“这本书的出版”“春天的到来”“她的走”和“长城的伟大”“柠檬的酸”这样一类“名词+的+谓词”(NP+的+VP)结构,我们觉得可以提出如下的新的认识:“名词+的+谓词”(NP+的+VP)结构是名词性结构,但不是偏正结构,而是由名词性标记成分“的”插入“名词+谓词”(NP+VP)这种主谓词组中间所构成的另一类“的”字结构。上述分析与认识跟传统的分析与认识有相同点,有不同点。相同点是都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春天的到来”是名词性结构。不同点是:第一,对整个结构性质看法不同——按传统的分析,这类结构是“定—中”偏正结构,修饰语是“名词+的”(NP+的),中心语由“谓词”(VP)充任;按现在新的分析,这类结构是一种名词性的“的”字结构,这种“的”字结构是由名词性附加成分“的”插入一个“名词+谓词”(NP+VP)这样的主谓结构中间所构成的。第二,对这类结构的“中心词”的看法不同——传统的看法是,这类结构的“中心词”是后面的“谓词”(VP),即所谓“中心语”,如上面所举的实例中的“出版”、“到来”、“走”和“伟大”、“酸”等;而按现在新的认识,即按中心词理论,这类结构的“心”是名词性附加成分“的”。第三,对“的”的看法不同——都将这个“的”看作“结构助词”,但以往认为它是个“名词性单位的后附成分”,意即只能后附;现在则认为它是个“名词性单位的标记成分”,它既可以后附,也可以“嵌中”。以上所述二者的异同,可列如下表(以“这本书的出版”“长城的伟大”为例):整个结构性质内部结构关系中心词“的”的性质传统的看法名词性偏正结构出版/伟大名词性单位的后附成分现在的看法名词性“的”字结构的名词性单位的标记成分显然,按新的分析与认识,原先用传统的观点来分析“这本书的出版”、“春显然,按新的分析与认识,原先用传统的观点来分析“这本书的出版”、“春天的到来”、“她的走”和“长城的伟大”、“柠檬的酸”这样一类结构所存在的两个矛盾——(一)整个结构性质(名词性)与作中心语的词语的性质(动词性或形容词性)之间的矛盾;(二)这类结构的所谓特殊性(整个结构是名词性的,作中心语的词语却是动词性或形容词性的)与布龙菲尔德向心结构理论之间的矛盾——就都没有了。按上述新的分析与认识,现代汉语里主谓结构跟结构助词“的”构成的名词性“的”字结构可以有两类:甲类:“的”字后附在主谓词组的后边,如“张三写的”“张三买的”和“个儿高的”“叶子宽的”等;乙类:“的”字出现在主谓词组的中间,如“这本书的出版”“春天的到来”“她的走”和“长城的伟大”“柠檬的酸”等。从语法性质上看,这两类“的”字结构,都是名词性的;从表述功能看,它们都具有表达指称的功能。但是,它们无论在表述功能、语法意义或语法功能上都有重要的区别。具体区别如下:从表述功能和语义功能看,甲类“的”字结构可以表示转指,也可以表示自指。拿“张三写的”和“叶子红的”为例,在“张三写的是诗歌”“叶子红的是枫树”里,“张三写的”转指写的东西,“叶子红的”转指某种植物;而在“张三写的时候”“叶子红的时候”里,“张三写的”、“叶子红的”都表示自指。而乙类“的”字结构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表示自指,不能表示转指。从语法功能看,甲类“的”字结构除了作主语、宾语外,还可以作定语、中心语、谓语等。以“张三写的”和“叶子宽的”为例,请看实例:(1)张三写的是一首七言诗。
叶子宽的是韭菜。(2)小说,我喜欢读张三写的。
韭菜,要吃叶子宽的。(3)张三写的那首诗有诗意。
叶子宽的韭菜好吃。(4)我买了两本张三写的。
那叶子宽的是韭菜。(5)那首诗,张三写的。
我买的叶子宽的。乙类“的”字结构则只能作主宾语,不能作别的句法成分。例如:(6)春天的到来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狐狸的狡猾是有名的。(7)人人都盼望春天的到来。
谁不知道狐狸的狡猾?此外,甲类“的”字结构经常用来提取谓词的论元,例如“张大夫用中草药治疗肺气肿”,这句话里动词“治疗”的论元有三个——施事论元“张大夫”,受事论元“肺气肿”,凭借论元“中草药”,当我们要提取其中的任何一个论元时,可以而且只能用甲类“的”字结构。请看:(8)张大夫用中草药治疗的是肺气肿。[提取受事论元](9)用中草药治疗肺气肿的是张大夫。[提取施事论元](10)张大夫治疗肺气肿用的是中草药。[提取凭借论元]乙类“的”字结构不能用来提取谓词的任何论元。上述新的分析与认识,跟朱德熙()、陆俭明()关于“所”的分析相一致,他们认为,“他所反对的”,作如下的切分比较合理:显然,“这本书的出版”、“狐狸的狡猾”作如下分析也不是新奇的事:值得注意的是,吕叔湘、朱德熙在《语法修辞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里就将“中国的解放”“态度的坦白”看作“主谓短语”,而将处于被包含状态的“自己不懂(的东西)”“中国人民获得解放(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看作“句子形式”,以示区别。而关于主谓短语,他们是这样说的:“主谓短语:一个主语加上一个谓语,中间用‘的’字连接,如‘中国的解放’‘态度的坦白’。”(《语法修辞讲话》,9页)显然,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乔姆斯基理论中的某些思想与观点来对汉语的一些语法现象作新的思考与分析。我们也曾用上述分析与观点给外国留学生讲解“这本书的出版”“春天的到来”“她的走”和“长城的伟大”“柠檬的酸”这类结构,效果相当好。因此,上述新的分析与结论对于对外汉语教学中有关结构助词“的”的教学,也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选自《互动与共鸣——语言科技高层论坛文集》互动与共鸣——语言科技高层论坛文集主编:李葆嘉ISBN:-7---0定价:78.00元喜欢这一篇,就分享到朋友圈欲查看年“世图语言学”精彩推送,北京看白癜风哪间医院效果好北京治疗白癜风那个医院比较好
转载请注明:http://www.pdnns.com/ways/62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