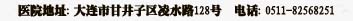母亲逝世整两年了。其间,我一直不敢拿起笔来面对母亲。母亲逝世的那些日子,我的心痛得快要碎裂了。一想起母亲,在暗夜中和无人处的我便止不住涌流的泪水。那么多的朋友不停地打来安慰的电话,我往往是未语泪先流,半天答不上一句话来。“写写母亲吧”,两年来,不止一个朋友在劝慰我时这样说。但我一直不敢面对这个题目,一直在逃避这篇文章。这半年来,也曾有几次,我坐在写字台前追忆母亲,但每次写不到十行,便难以自抑,写不下去。今夜,刚刚动笔,我的泪水又涌出了眼眶,以致我不得不又一次放下了笔。
慈爱的母亲逝于公元两千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农历十月二十四,那个北方高原最寒冷的冬夜的子时(凌晨一时多)。那晚,我刚扔掉书睡着,突然被电话铃惊醒,一看来电显示的号码,我的心便揪了起来,是父母的电话!几年来,我出差从不敢关掉手机,就是怕误掉这个电话,但每每最害怕接的,也就是这个电话。电话那头,二弟媳急急地说,妈病得厉害哩!电话里同时听见母亲的声音:“不要叫,谁也不要叫,黑天半夜的……”我一边嘱她先给母亲吃药,一边拉着外衣往门口走,脚未跨出门,电话又响了,电话那边带着哭腔说:“快点儿!不行了!”等我跑下楼拦到出租车赶过去,母亲已走了。距母亲住所只有半里路远的大姐和二弟站在母亲的床边,父亲在床上坐着,和二弟媳领来的一个亲戚女孩扶着半靠在被子上的母亲。母亲的脸和手还是热的,苍白的头发里汗津津的。我把耳朵贴到母亲的心口上和鼻孔上,已再也听不到一丝生命的呼吸了。我要弟弟妹妹们再催延安这指靠不上的“”,医院去抢救,父亲指着母亲牙缝里渗出的一星白沫,说,不行了,不要去了。但我仍不甘心,坚持用刚刚赶到的“”急救车上的担架把母亲抬上急救车,医院的急救室,从心里强烈地期盼着现代医学能出现奇迹,把母亲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然而,一切的抢救办法都已无效,母亲走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怎么也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但残酷的现实就摆在了面前,任谁来也再无回天之力。一直到今天,我仍不敢回想把母亲的遗体往回接时的心情。几个时辰前还是活生生的母亲,转眼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怎不叫人痛断肝肠!因考虑到我住的地方是机关家属院,工作多年来熟人太多,不愿惊动大家,也不想让母亲的事情过得太大,与二弟两口子商量后让急救车开到了东关保养厂家属院。我们把母亲的遗体抬上楼停放在二弟家地板上,让母亲在上山之前再在儿女的家里歇息几天,也让孩子们 再陪她老人家几天。嘱弟妹们照料好母亲,我和大姐连夜赶回乡下老家取大姐早几年就给母亲准备好的寿衣。一路上,我的泪水一直在脸上涌流,内心却还在祈盼着能有奇迹出现,不是常常有逝去的人又复活的报道吗?等返回城,天已快亮,大姐、三妹和小妹给母亲擦洗过身体换上寿衣后,在一位远亲长者的操持下,兄弟姐妹们给母亲送了“终”。至此,我终于放弃了一切幻想,从心里承认了这样一个冷酷的现实:母亲走了!母亲永远不会再醒过来了!随后的几天,我不知是怎样度过的。白天,忙着上山给母亲修陵,晚上,在寒风中给母亲守灵。此时的母亲,神态安详,如熟睡中一样,而且睡得是那样的安恬、幸福,嘴角似有一丝微笑。人们说,恶人死了后面目会变得很狰狞、恐怖,而善良的人逝世后神态会很安详、好看。弟兄姐妹们争抢着坐在或躺在母亲的身边,大家都非常珍惜这与母亲的身体相处的 的时光。平时胆小的妹妹们谁也不知道害怕了。燃香焚纸时,我们总不由得去抚摸母亲的面额和手,此时的母亲,已浑身冰凉。母亲的身体在我们能看到触到的时光,只能用个数的天来计算了。23日凌晨,黄陵来的风水先生在走之前要到母亲的陵地“破土”“点穴”,我与三妹夫陪着他凌晨5时出发,6时赶到山上。这时,天还黑得厉害,山上什么也看不清。我们坐在湿漉漉的枯草上等待天亮。这时,母亲陵地右边的山谷里,长久地响着一只猫头鹰凄厉的叫声,我的泪水不住地流着:母亲,您一生善良胆小,几天后,您就要一个人住在这荒僻的山谷里了,母亲,您害怕吗?……按照乡俗,在母亲的娘家人、我们的舅舅的安排下,母亲上山的 天、第二天和第三天的傍晚,我们兄弟四人在三表兄的带领下去给母亲送夜火。我们从城边渐次送到母亲安歇的陵地。弟弟们带了好多干柴,红红的火苗在黑色的夜空里飞腾。我木木地跪在火堆前,听弟弟们在三表兄的指教下,一个个虔诚地说着:“妈,不要怕,有火照着您哩”“妈,把火都拿上……”在红火的映衬下,荒僻的山谷显得更加漆黑、幽暗,我的心也更加痛楚。我不知道,这些送给母亲的火,能否长久地在这黑暗的山谷里陪着母亲;是不是像舅舅说的,有了这些火,胆小善良的母亲就不再害怕了……母亲患冠心病和肺气肿已几十年了,因为经济原因,从来都是在家里吃点儿药,只有到非常严重,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厉害到快要放命的程度,医院住院治疗一段时间。一旦病情缓解,便催着要出院回家。所以,一直没有得到好的治疗。勤劳要强的她,一直在家里不停地干活。虽然,因为一直有病,十几年前,我们已为她准备了寿木和寿衣,但总觉得她还不到走的时间,所以,陵墓一直未修。她一躺倒,修陵便成了 的一件事。按照她的心愿,我们在距城较近的河庄坪乡石头村双龙河蟠龙山给她选了块陵地。仿佛天也苦悲,洒泪披莹。母亲一跌倒,好好的天气骤变,一整天的大雨之后又是大雪,泥泞、陷坑和滑溜,使得任何机械都不敢走,大家都很着急。叫人宽心的是,第三天,雪霁天晴,气候回暖,各种材料很快运进沟背上了山,修陵的进度加快了许多。26日下午,陵修成了。土工和砖匠们说,这个老人行了善,老天爷为这老人开眼了。母亲一生善良,与世无争,在帮助人上恐怕是这世界上再也难见到的热心肠了。在国人皆饿的六七十年代,榆林地区下来的讨饭的特别多,几乎每顿饭门前总要过去几群。尽管锅里的饭本来就不多,尽管为了让我们吃饱一点儿,她总是 吃点儿锅底,或者用更差的粮菜另做一点儿,但对于寻吃讨要的,她总要从锅里给他们匀出几勺来。有时饭不熟让他们坐下等。说咱少吃上一点儿,这些可怜人就饿不坏了,世上谁能没个难处呢。我们所住的甘谷驿镇,是三县交界(延安、延长、延川)的古驿站,更是三县 的一个集市,对于那个年代坐不起车、住不起店的城乡亲戚,我们的家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旅店”。对于上门来的亲戚,母亲总是倾其所有地给他们帮助。给他们吃,给他们住,给他们解决一切只要是我们家的力量能解决的困难。记得十来岁时的一天傍晚,因城里武斗,一家表亲从延安城往黑家堡后沟的老家走,母亲拦住他们不让走,刮干面瓮底,又让我们姊妹几个抱着磨杆在月亮地里推那沉重的石磨。第二天,她把我们都赶到大门外去,用那磨下的一点儿面让遭难的客人吃好。对遇到急事难事的人,哪怕是找人去转借,也要帮他们渡过难关。即使对 过我们的人,母亲也从未想过找机会出口气,总是希望用恩化怨,对遇到难处的他们也施以真诚的关心和帮助。记得一位姓金的公社社长当年曾助恶人迫害过穷困善良的父母,那人后来犯错误被开除到乡下后偷了农民的牛和马去山西贩卖,被抓回后甘谷驿正逢集,人山人海地拉在戏台上被一些人拿大木棒打,浑身衣服被血浸透。母亲说,这些人怎这样残,把一个活人就硬往死里打,那个人尽管当官时是做过伤天害理的事,现在又偷了老百姓的牛,但他毕竟是条人命嘛,窑里还有老人婆姨娃娃一群要活哩嘛。有一位堂嫂极糊涂厉害,无缘无故地多次谩骂母亲,老实怕事的母亲只有忍着躲着。某一年,她的孩子夭折了,母亲听到后伤心地落泪,说那堂嫂怎么这样的命,一个亲亲的娃娃怎么就“撂了”。为了让她少点儿难过,拖着病体的母亲主动出面抱着那未成人的孩子与堂兄去老远的三道湾后的高山上送。母亲娘家户大人多,安排葬礼时,父亲决定只让侄儿辈来,侄女和孙子辈就不要来了。但听到母亲逝世的消息,计划中不让来的人也早早地赶来了。扶母亲上山那天,穿孝衣的孝子白花花跪了半架山,石头村的人们说,这个老婆婆好福气,这么多的孝子来送行。母亲的善,也是这世上恐难再见到的。自己喂大的鸡,过年时不忍宰杀;喂肥的猪,临交售的前几天,她总要站在猪圈旁掉眼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在枣园职业高中上班,一天,小妹妹上来,说这一向母亲和父亲光生气,谁也劝不下,她只有撵上来寻我回去解劝。我赶回去一问,母亲回答的原因竟是叫谁也想不到。原来,随着兄弟姐妹的上学、就业和进城打工,家里的老牛已无人放,也无人割草喂了,父亲把老牛牵到集市上卖了,但很快又被母亲挡了回来。母亲说,她到集市上问过,那些买牛的都是些无情无义的杀牛贼,他们把老牛买到绥德,用酒糟充上几个月,便杀得卖肉了。母亲说牛是保江山的,宁可便宜一点儿,也要卖给乡下的农人,让老牛多活些年头,最起码 不会挨刀子。那时,我们那一带的人对牛是不宰杀的,牛的归宿一般是老死或从崖上跌死。老死跌死后埋掉。母亲在的时候,平平淡淡的日子,没有感到那些日子的珍贵。尽管我常要求姊妹们要常想着母亲身体不好,要抢着行孝,如等到光景都过好,饥荒(债务)都开完,恐老人就不在了。但实际生活中,我自己就常做得不好。在母亲面前没耐心,常为她的爱唠叨发脾气。这是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事。她总是在关心着你,即使炎热的天气使你一刻也受不了,好容易熬到散会回家,脱掉上衣光膀子想尽情地享受一会儿凉爽,想抢时间休息一会儿,她会不停地走进房来,看你睡着了没有;怕你凉着,轻轻地把被子给你盖上。你气急败坏地把被子扔到一边后,她连声说:哦,哦,不盖了,不盖了。但没等你睡着,她又蹑手蹑脚地走进来,轻轻地给你盖上一块被单或毛巾被。被这没完没了的关心扰得睡不安稳的我与弟弟们往往不是向母亲表示感激,而是更负气地把被单或毛巾被扔到一边去。出门时,她每次都要撵到楼道反反复复地嘱咐你,或撵不上时趴在窗台上向你喊:过马路要操心,上车下车要操心……好像我们还是小孩子。每次给母亲发过脾气,我总要恨自己为什么不控制自己的脾气,为什么要给母亲发脾气,并给妻子和姊妹们说,一旦没人这样唠叨你,麻烦你,那大海一样深的母爱,你就再也没有了。有这样一个人这样对你,是你的一种幸福。话虽这样说,但一到下一次,又对母亲的关心不耐烦了。星期天和节假日买些鸡鱼蔬菜回家,母亲每每要走进厨房动手帮忙,但我总觉得既然儿女们回来了,她就应该坐在沙发上等着吃,一次一次地把母亲劝出去。现在,我才明白,母亲一次次地走进厨房,一是出于她勤劳一生的本能,更是想和孩子们在一起说话做活呀,我怎么就不去理解母亲,就不去体谅母亲的心呢。一段时间,我在外地出差,粗心的弟弟们下班后只顾了与朋友们应酬或忙其它事,几天见不到孩子们的母亲每天几小时几小时地站在窗前望气象局的大门。大概那时,大家都觉得还早,一切都还好,母亲还不到走的时候,也就麻痹大意了。那个寒冷的冬夜母亲一走,猛地感到父亲母亲,是为我们遮风挡雨,守护生命的背靠的大山;是我们清贫的童年永远燃着炊烟,烧着热炕,熬着米汤,腌着咸菜,蒸着窝头的老窑啊。母亲的离去,仿佛背靠的大山轰然垮掉,温暖的老窑骤然坍塌,原来被父爱和母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我们的四面猛然敞开,猛烈的风暴裹着雨雪一下子扑进来,肆无忌惮地欺凌着再也无人遮风挡雨的我们。在精神上,我们再也没有一个躲避风寒的地方了。母亲走了一年多,我陪父亲回甘谷驿老家整修老地方。看到院子当中的“春锅”(老家对院子里垒的夏天做饭的锅灶的称谓),心里感到既亲切又难受。记得,少时夏天的晌午,从山上回来的我们都在凉爽的窑里歇晌,母亲一直在太阳底下忙着给我们做饭。晌午饭几乎每顿都是和面。母亲先是炒上一大盆菜,或豆角洋芋茄子,或葫芦南瓜洋柿子那些自家地里上来的菜;再擀上一大块杂面或玉米面。擀面的同时烧上一大锅水。水开后把面下进锅,再把菜和进去。那时,在我们心中,这就是 吃的饭。因买不起煤,柴也很缺,我和弟弟在延河发洪水时捞回的河柴大多是碎末末柴。太阳底下,母亲不但要做饭,而且还要拉风箱。吃完饭后,我们去上学或上山,母亲还要赶着收拾锅灶和喂猪、饲蚕,这些活做完后锄头一扛又要去生产队上工。有时忙得顾不上吃饭。母亲是多么地劳累啊!可恨我们那时竟不懂得心疼母亲,没有给母亲帮多少忙。现在想起,心里不知有多少悔恨。照看地方的借住户问如何处理院中的春锅时,我一口说道,留着,永远保留着!那些过去了的岁月,是多么地叫人怀恋啊!我们生长的老院,处处有母亲的影子,一想起就叫人眼睛发湿,心头发痛。一眨眼,仿佛又看见童年时的我们,如一群羽翼未丰、飞不出窝的小雀,眼巴巴地盼望着衔着吃食的母亲从山上归来。她从自留地担回的红薯南瓜玉米豆角是我们秋天 的也是 的食粮;一下又想起端午的清晨,睡眼蒙眬的我们感到耳朵上被母亲夹上一枝沾着露水的清香的苦艾,便闻到了锅里飘出的粽子的香味。紧接着被母亲一个个叫起,洗过脸后尽情地吃那喷溢着黄软米大红枣甘甜和新鲜的绿粽叶嫩马莲清香的刚出锅的热粽子;又看见童年时的清明节,围在案板旁,母亲给我们教怎样捏“燕燕雀雀”。母亲的手很巧,一块面拿在手里,三下两下,一只燕子、凤凰、猴子、兔子或蛇的形状便出来了。用梳子在鸟翅上按几下,用剪子在动物躯干和四肢上剪几下,那些鸟和小动物便毛发娟秀,飘飘欲飞。 用红枣皮把嘴吻一沾,用黑糜子或黑豆把眼睛一点,一只活灵活现的小鸟或小动物便出现在我们面前。现在,每年清明,只要有时间,我总喜欢动手给孩子们捏一串“燕燕雀雀”,喜好和“本事”就是那时候母亲培养的。每年清明,母亲都要专门给我们姊妹捏分属于各自的“子推馍馍”。给我和弟弟们捏的是虎头虎脑的胖“老虎”,给姐姐和妹妹们捏的是附着了许多精致美丽小飞禽和花草的灵巧秀气的“抓髻”。“子棰”之外又给每人捏一串活灵活现的“燕燕雀雀”。吃完“老虎”“抓髻”后,放学后或山上干活回来,我们一天一点点地吃那属于自己的已风干得脆硬的“燕燕雀雀”。每年中秋节的前一两个夜晚,母亲都彻夜不歇,跟左邻右舍一起相帮着炉月饼。而过年,更是我们这些农家孩子最渴盼的节日。不管多困难,实在挪不开时哪怕去亲戚家转借,也要想办法买点儿猪肉、粉条、白菜之类的年货,家里自做一锅豆腐,炸一老盆油糕和油镆镆,再做上一两只鸡的酥肉、丸子之类,让孩子们的过年也与其他人家孩子的差不多。由于那个时候我们还都小,父亲白天晚上忙山里的活或村上的账,也不会做饭。早上的便餐、早餐后的上山祭祖、祭祖回来的饸饹,都要母亲一手操持。冬天日子短,往往等收拾完饸饹锅天已快黑。母亲又开始准备年夜饭,又要做菜又要过稠酒,常常是饭不熟我们便瞌睡得等不上了。母亲边自责边做菜,边给我们讲“毛野人”的故事,生怕我们睡着吃不成那些我们一年只能吃一次的好饭。清清贫贫的日子,由于母亲的节俭操持,过得依然有滋有味,给我们心里留下了那么多的一辈子也忘不了的美好记忆。母亲做的稠酒,是截至目前我喝过的 的饮品。那是用麦麸、酒曲和酒谷米做的真正的地道的粮食酒,醇厚的甘甜中略带些微的酸。非常可口,不含一丝酒精。那年腊月我从风雪边防线回来,过年晚上一口气就喝了五大碗。年腊月,母亲病情突然加重,我们赶回去接她上延安住院,她拗着说什么都不走,说她知道她的病,既然非走不可,过年是肯定回不来了,而她一走,我们姊妹的这个年肯定喝不上稠酒了,硬撑着把酒做好放在瓮里发酵才答应起身。这时,她已病得连车也扶上不去了。那时,远在黄陵的同学胡向东每年正月都要来甘谷驿看望母亲,喝母亲做的稠酒。偶尔一年来不了,母亲总要先给他匀出一份留着或捎下去。今天上午,他与我们姊妹一起去山上给母亲烧纸,跪在黄土地上祭祀完后,大家在母亲陵前的山坡上合影留念,都感慨自母亲走了后再也没喝过稠酒了。比起母亲做的稠酒,那些宾馆酒楼和市场上所谓的稠酒,根本就无法入口。我们再也喝不上母亲的稠酒了。母亲在延安居住的三年,每次去看她,她都不想让我们走,总想留我们在她那儿住,跟她和父亲拉话。但忙于生计,只要有弟弟妹妹们在时(除请一个保姆照顾外,我安排每周每家一天陪母亲拉话,白天忙自己的事,晚上去招呼),我满足母亲愿望的时候并不多。最叫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是母亲走的那天。我因前一天晚上刚从西安出差回来,好几天没见母亲了,第二天上午与妻子专门去市场上买了一条鱼和一只土鸡。过去后小妹早上做下的鱼还未吃完,便放下未做。下午与母亲一起吃过饭后,动身去杨家岭中学家属楼接女儿。母亲从房里跟到楼道,不停地说不要回去了,晚上就在这儿住。我考虑第二天早上要上班和送孩子上学,加之二弟家打电话说,他们下班后过来,又拒绝了母亲的挽留。谁料,这一走居然成为与母亲的永别!几个小时后,母亲便永远地离我而去了。这件事让我痛悔终生。我恨自己为什么要回家去,为什么不在那个晚上陪陪母亲。这个遗憾成了我心中永远的伤痛,至今一想起就心里憋得难受。作为母亲的长子,母亲走的时候,我应该守在母亲的身边。母亲告别这个世界时,应该是靠在我的肩膀上的。可是,我没能。
母亲没接受过学校教育,但承自传统和出自天性,她崇敬一切天地神灵,尤敬观音菩萨。她相信穷人善人的命有老天爷照应,她相信恶人坏人最终都要遭报应。她说,人要有怕心,怕天怕地,怕做了亏心事遭报应,这样的话,世界上的人才能都平和一些,都善良一些,穷人富人善人强人才能都在这世上活。她关心和同情所有遇到的穷人和困难者。与人打交道时信奉的道德准则是宁可吃亏不可沾光,也常常这样要求我们。对孩子们的爱,更是达到忘我的地步。我们一个个离开老家后,每年的二月二,她都要站在老窑的门口一个一个地念着姊妹们的小名“叫魂”。这一切,直到那年我们把母亲接进城后二月二的晚上她从姊妹几家挨着往过走时才知道。都已上学、工作的兄弟姐妹们已不相信这些,便劝阻她拖着个病体东关南关北关这么大个城里七八家地往过走。尤其是我们兄弟几个,坚决拦着不让她这样做。但最终,谁也阻拦不了她。谁拦她,她就不在谁家住了,说她心慌,急着要回清凉山上的家去。三弟的孩子过生日时,大家又拿这个事说她,她说她几十年就是这样过来的。说老家人说她的孩子一个个平安健康,就是由于她每年二月二给孩子们叫魂。她说,娃娃们在外边做事,风风雨雨,塄塄坎坎,难免有个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失魂落魄,迷失方向,她一叫就回来了。说亲生父母的声音,孩子们在千里路上都能听见。那个时候的母亲,叫人又心疼又生气,但谁也没办法,谁也改变不了她。读书前的我,是一个让母亲费心的山村野孩子。放学后晌午不睡觉,跑去陡峭的崖洼上“溜绵土洼洼”或钻进草林里找毒蛇和马蜂打。又私自下河学会了耍水,母亲一不注意便跳到河里去了。稍大一点儿后,跟一群娃娃分成上城下城两支队伍,一支据守古城堡一支进攻。天地不怕的交战双方使用的武器是一挨上身就飞血溅肉的石头块子和干胶泥疙疙,经常是浑身挂彩流血,让母亲常常撵着寻。一年级那年,被一群高年级同学追着“飞”下几丈高的城墙摔在硬石子铺的城东门口,昏迷了几天几夜,母亲抱着未合一眼,险些急死。为接摔骨折的腿,母医院看。记得那时甘谷驿到延安城的路是顺河湾转,交通工具是骡马大店的马车,从大清早一口气不歇地走到傍晚才进了东关。十八岁那年,不愿意守在家里,非要去从军,梦想在战争中一刀一枪拼个前程,在风雪边防线上一干就是四年。那个时期中苏关系紧张,双方在边境上陈兵百万,尤中越战争时局势危如累卵,千钧一发。上了前沿阵地的我们都给家里写了遗书(部队保存准备一旦牺牲就寄回老家去)。那段时间关于新疆中苏大战内地流传着好些版本。有的甚至说为了将攻进新疆的苏联军队彻底消灭,中方以核试验的形式在新疆投放了原子武器,致使我们的防区玉石俱焚云云。偏军情紧急家信及时寄不回不去。同乡野狐沟村战友康斌成的父亲到我家说新疆兵的骨灰盒已运回延安,叫父亲与他一起去看有没有我和他儿子的。那些消息对父母的打击是非常之重的。父亲常常是半夜正睡着一下跳下炕外衣也等不及披就往马路上走,说窑里憋得心要炸。母亲更是愁得一夜一夜地坐着不睡。解甲后农村兵被轻轻巧巧地甩回农村,偏我又自命不凡不愿顺祖辈们的老路早早成家过光景,剃了光头光着膀子白天拼命地掏地割麦担粪,晚上一黑了一黑了不睡地复习旧课。让母亲心疼、发急,不知怎样才能让儿子心里不难受,才能不这样瞎拼命。老家的那些老年人常说,儿女是前世的仇人,这世是讨债来了。出差或回老家,一看见桥儿沟、李家渠的河湾和甘谷驿的学校和城墙,便又想起了小时候的事。唉,让母亲为我操了多少心,受了多少罪啊。因父亲腰腿有病,在相当长的时间,母亲是这个家庭的主要劳力,承担起了这个家的主要负担。春种秋收她要受罪;那极难见利,麻烦至极,但对一个贫困的农家极为重要的家庭副业,更是全压在她的肩上。一年四季养猪,是母亲农活之外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小猪喂到一两个月,便要逮出窝去集上卖。本镇集上不好卖时,母亲便挑着去三十里外的姚店子集上卖。那些年好像常遭旱灾,贫困的农民抗灾能力弱,天一旱猪便没人要。母亲常是天刚亮便起身,走上三四个小时,到集上后不吃饭不喝水,一直站到太阳落。运气好一点儿时,半后晌能卖掉赶回家。运气不好天快黑也卖不掉一只,又饿又累的母亲又得把那重重的小猪担回来。姚店子到甘谷驿那个时候路不好,要转很多大湾。因那些大湾坡陡弯急,经常有骑车人摔下去或有车翻下去,便留下了一些阴森恐怖的关于死人和鬼魂的传说,胆量小的人晌午都不敢从那里过。为了孩子们能念书,胆小的母亲便硬着头皮往过走。母亲说,每到那些大湾前,她总是前后照看有没有过路人。能有几个人往过走还好。照不见人时,便要一个人硬撑着胆量往过走。说她一个人往过走时头发根子紧绷绷的,怕得衣服都汗湿了。那时,我们都小,也不敢走得很远,只站在古镇西门的城墙上照母亲。有一回天阴,母亲走到谭家湾,已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了,实在不敢走了,上到村子里在一个老婆婆家借宿了一晚上。我大一点儿后拉着架子车跟母亲去姚店子卖小猪,路过谭家湾时母亲常给我指那个老婆婆的院子。我对那个好心肠的老人充满了感激之情,她让母亲免受了一个漆黑之夜的惊恐害怕。但因那时小,不懂事,长大后为了谋生又天南地北地奔波,加之母亲有病出门也不方便,一直没机会去打问看望那个老人。现在,那老人肯定已不在世了,报答她的心愿再也无法实现了。母亲还养蚕。辛苦一个春夏,当扫签枝上结满了洁白的茧子,预示着我们的学费和书费又有了着落。那年什么副业也没法搞了,母亲领着我们每晚把红薯放在木盆里剁。熬了一个冬天,提炼出几十斤芡粉,请人漏成粉条后,领着我踩着冰河背到黑家堡乡寨子川的水利工地上卖给了民工灶。回来的路上,母亲一直在自责受了一个冬天罪,漏了一场粉条,没让孩子们吃一顿,也没给亲戚们送一点儿。我劝母亲,家里用钱紧,我们谁也没想吃,亲戚们以后有了再给他们送。母亲一直在叹着气,说她心里难受。一度时期父亲腰痛得不能上山,家里已陷入赤贫状态,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成了问题,有一个秋天就是我和弟弟去延长老山沟里打的野棉蓬籽度过的。村上人都笑话那么穷还让孩子都上学,亲戚们也来劝母亲。但主意坚定的母亲坚决不同意任何一个孩子回家跟生产队上山挣工分,说再难也不能让孩子们不上学。在母亲的坚持和艰苦操持下,我们姊妹八个都没有辍学,三个上了大学,两个上了中专,另三个因时代原因只上了高中,为以后的工作生活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生活压得母亲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心里不好活,一生与娱乐无缘,好像从来没唱过歌。搜索全部记忆,只记得母亲唱过一次歌。那是在我十岁左右时的一个冬天的夜晚,半夜时分,我醒来了,躺在被窝里看还在做活的母亲。白天在庄稼地里劳作了一天的母亲坐在前炕边纺线,满脸悲苦的她哼着一支歌,歌词我没听下,只记得那歌调子极悲凉极伤感,让人想流泪。我想,母亲的生命里,艺术的天赋应该是很高的。我们兄弟姐妹文学、音乐、美术的感觉明显超于周围一般人。尽管由于成长环境所限,没几个成大器的。我和二弟在中学时都是校乐队的骨干,自学的识谱能力都较强,上学时中学音乐教师唱不准的新歌常来请教我们。二弟在农村靠自学二胡达到舞 奏的水平。三妹上的是音乐专业,三弟学的是美术。姊妹们都以自己的特长在社会上谋得一席生存之地,这要归功于母亲给我们的生命遗传。在繁重、艰辛的农家生活里,母亲好像没有任何爱好,白天晚上不停地做活。接到城里后,姊妹们什么也不让她做。事实上,在单元楼里也就没个什么做上的。我现在才想,这对一生勤劳的母亲,其实成了受罪和折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母亲对养花种草有那样高的热情。对我和三妹搬过去的几盆花,她拖着病体白天端出去,晚上搬回来,浇水、搭架,不停地侍弄,不知费了多少心。怕她冠心病不堪承受,我几次威胁母亲,她要是再每天端出端入,弯腰出力,我就要把花都扔掉,她连忙答应再不端了。一盆绿草蔓上开些小红点的不知名的花儿,她喜爱有加,用线绳把那长长的蔓草绑在窗子上,因炎热的夏天不好开窗子,我过去一次,解开绳子扔掉一次。年10月2日晨母亲突发脑梗入院治疗。第四天,刚刚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正巧来看望母亲的张晓辉兄捧来一篮鲜花,母亲睁开双眼长时间地盯着看。因医生治疗时说病房小有点碍事,父亲把花篮放到楼道里去。当时的母亲还说不清楚话,但眼睛四处不停地张望,半天找不到后吃力地问父亲“拿到哪儿去了?”我这才从心里感到母亲对花儿的真爱,赶忙到楼道拿回放在母亲的病床对面。母亲出院后一位朋友送给我一盆长年盛开不衰的玻璃翠,晶莹剔透的茎秆上开满了星星般的粉红色的小花,我早就要送过去,又担心车上挤坏或路上冻坏,总想有顺车时再捎过去。母亲逝世前一天中午,天气非常好,我装在塑料袋里提过去,放在母亲的窗玻璃前,说,妈,您看这盆花好不好?母亲笑着说,好。我说放在这儿,您天天都能看。出院整一个月的母亲刚能扶着桌子走路,她走到窗台前看着,笑着说,好,就放这儿。谁料想,这花儿,母亲只看了短短的半天。我为什么不早点儿打个车送过去呢?为什么不早点儿了解、尊重母亲的爱好,买上几盆常开的花送给母亲呢?把母亲接回二弟家的 天傍晚,黑龙沟恰巧进来一个卖工艺花的小车。怀着对母亲的崇敬,我选了颜色、式样都非常好看的八盆端上楼摆在母亲的灵前。第二天,又让妻子去花店买了一簇与寿木等长的鲜花,连同二弟家的一盆君子兰并小弟去乡下采回的柏树叶摆放在母亲的身边。母亲上山那天,我们把敬献给母亲的花儿全捧上山,献在母亲的灵前。母亲,您那么爱花,把这些花都带走吧,让它们天天陪着您,让您在 上也生活在鲜花丛中。扶母亲上山的第二天,父亲和舅舅带我们上山去给母亲“复山”。祭奠完毕后,八岁的侄儿点点跪在母亲的陵前把头磕得“咚咚”响,突然一股旋风从陵前升起,围着我们转了几圈后,卷起一块黑纱笔直地冲上几十丈高的天空,在无风的山谷里越飞越高,越飘越远,一直往老家的方向飘去。大家站在山上一直望着那长长的黑纱成为一个小黑点, 消失在浩渺的碧空中。表哥和表嫂说,是母亲显灵来看孩子们来了。我虽然猜想可能是冷热空气对流造成的奇异现象,但从心里,也真希望母亲能看到孩子们祭奠她来了。母亲在时, 兴的就是儿女和孙子们都回到家里,热热闹闹,红红火火。今天,我们都来了,母亲,您看到了吗?在母亲的陵前,眼前全是母亲与我们在一起时的情景,感受到的全是母亲对我们的爱。望着洒满阳光的逶迤的山岭,我从心里默默地对母亲说,母亲,您安息吧,不要再愁孩子们了,我们都长大了,小弟也已成家了。母亲,我们会继承您的厚道善良,会与人处好的;我们会继承您的勤俭勤劳,会把光景过好的。母亲逝后的那些个夜晚,经常梦见母亲又复活了,高兴地喊弟弟妹妹,眼睛一睁开,却发现是梦幻,又陷入无边无际的哀痛之中。为了打发那漫漫长夜,出差的旅途中,每到一个地方,我总是先到书店去买几本书。读《曾国藩》《张居正》《乔家大院》和《大清相国》等,看到古代的“守制”制度,竟觉得是那样的好。那些能解脱一切俗事,在母亲陵墓旁结草为庐、静心守孝三年的人,是多么地有福啊。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我知道,我是不会有此福气的。我们回报母亲的,不及母亲给我们的万分之一。母亲姓高名讳凤兰,延长县黑家堡乡碾子洼渠人。蛇年生人,逝年七十五虚岁,查《万年历》诞辰为己巳年农历四月初三,公历年5月11日(民国十七年)。母亲在时,最害怕误最害怕接的是母亲的电话,故母亲用过的几部电话的号码都刀刻般印记在脑子里。母亲在老家时的电话号码是,从甘谷驿初搬到延安清凉山二弟家的窑洞时用的电话是,租住气象局家属楼时的电话是。我再也接不到母亲的电话了。农历乙酉年十月二十四日深夜于高家园子苏冠华sgh